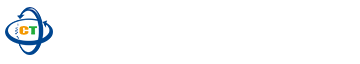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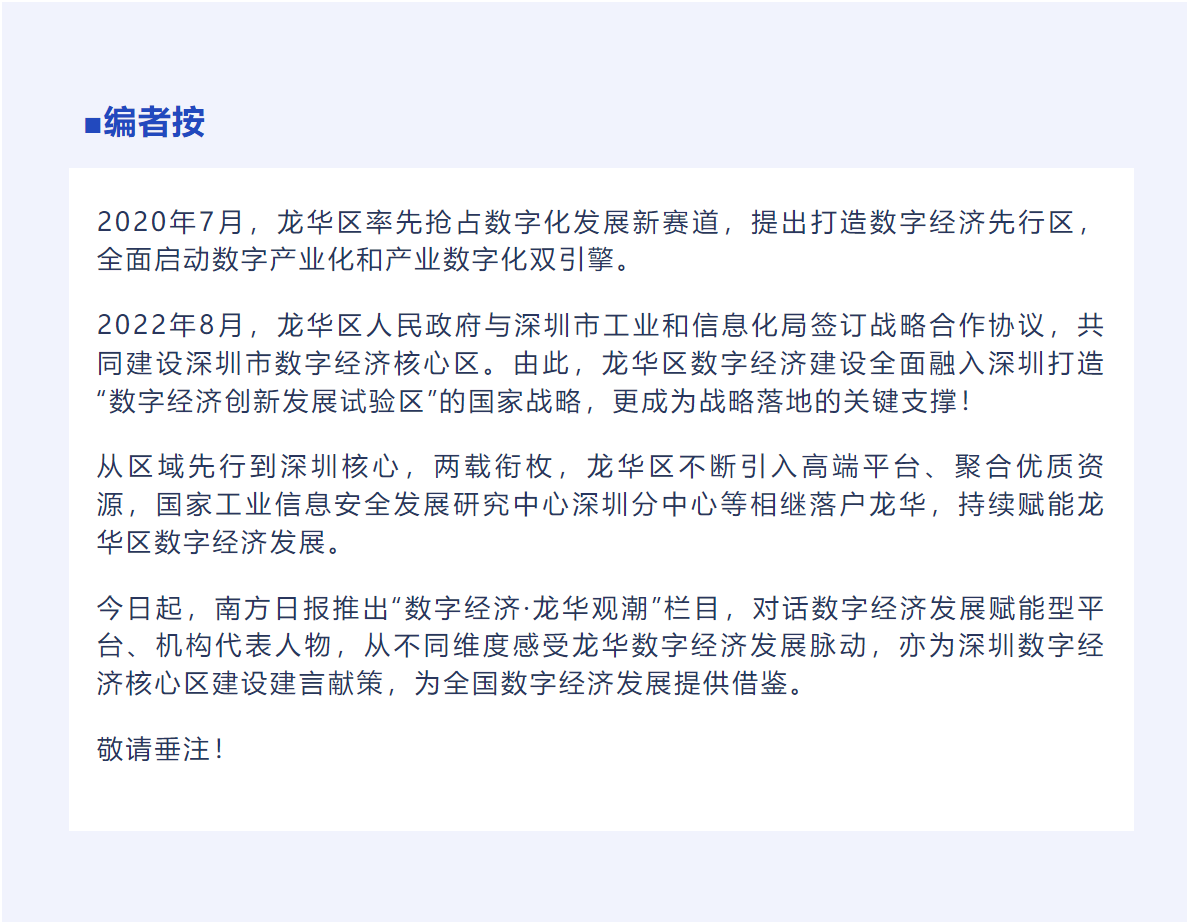
1999年,宋勇华进入富士康,从2级工程师一路做到富士康集团中央数字化MES技术委员会总干事,一干就是18年。在集团中央下辖软件公司捷达世主导富士康集团MES后,因该软件公司解散,他离开富士康,转换跑道,与曾经并肩作战的伙伴一起创立了灿态信息,开始专注于制造业企业的工业数字化软件服务。
宋勇华喜欢用马拉松来总结自己的人生。在他的人生历程中,第一场马拉松是他在富士康18年的职业生涯,这个期间,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工厂信息化和智能化;第二场马拉松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在三年半里跑遍全中国60多个城市,跑了134场马拉松;如今,创业是他人生中的第三场马拉松。

“我觉得智能制造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也应该像跑马拉松一样,需要持久的耐力和坚持。”宋勇华说。
在龙华区奋斗了23年,积累了155个案例、42项专业发明,宋勇华无疑是龙华这片热土上最接地气的数字化转型技术人才。
而在人生的第三场马拉松中,宋勇华发现,认知、成本和基础,已经成为制约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因素。他尝试用独创的表达重新解读数字化,统一被服务对象的认知,并以“庖丁解猪”式手法,创新产品模块,对接企业的转型痛点。
最重要的是,在与中小企业的同行中,宋勇华敏锐地发现,现场工程师的短缺,才是制约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后一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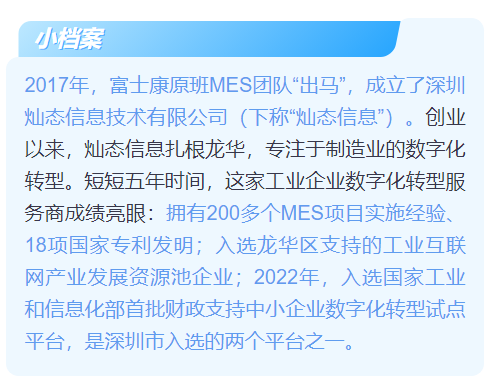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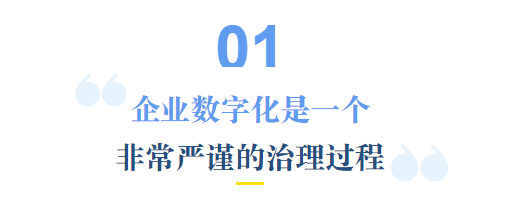
南方+:您在富士康呆了18年,干的也是与富士康数字化转型紧密相关的岗位,如今,富士康是全球电子科技制造服务领域数字化转型标杆,我们很想知道,富士康的数字化转型是怎样的?
宋勇华:早在1999年我进入富士康的时候,富士康就被逼着开始了数字化转型。当时我们称之为信息化。为什么说是被逼着?因为富士康是全球产业链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一个集大成者,苹果、思科、诺基亚等国际知名品牌都主要由富士康代工。
全世界顶尖的产品都在富士康制造,意味着全世界消费者的眼光都盯着这里,所以,品牌方就要求富士康做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方式。比如,苹果公司要求富士康在100天内出货近亿台iPhone手机,那么,每一天应该备多少料、出多少货?什么时间能交货?这些都不是你拍着胸脯能保证的,品牌方要求你必须用数据说话。他要从第一天就盯着你,确保备料、生产、交付的各个环节都能按时完成,而不是等到最后一天,听到你一句“对不起,完成不了”。
所以,企业的数字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治理过程。我深刻地记得一个案例。那是2013年,富士康要在郑州航空港8平方公里土地上紧急筹建工厂。一开始,负责筹建工作的八位部门主管给出的时间表是6个月,郭总裁当场拍了桌子说,“一支手机的生命周期是三到六个月,六个月生产才启动,大家就都不用干了!“。最后他要求,6个星期,第一台IPhone必须出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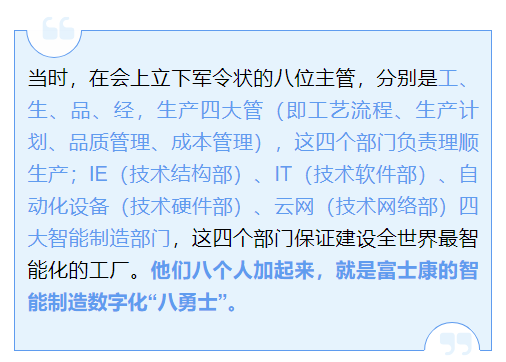
南方+:听起来,富士康的数字化转型非常令人震撼,这个过程又如何成就了您和灿态?
宋勇华:当时,我作为富士康数字化MES技术委员会的总干事,参与了郑州苹果智能工厂数字化的建设。这么多年,富士康为众多国际品牌代工,而我一直是富士康中央资讯软件服务团队中的一员。我先写了八年的代码,之后又干了十年管理,从工程师2级一路干到MES技术委员会总干事。尤其是后期的管理工作,我一直在系统梳理行业特点、产业匹配度、人才应知应会,从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产业知识。
可以说,富士康的数字化转型是一路被国际品牌监督的鞭子抽打着前行,而我也在这个鞭打的过程中,沉淀出了自己的能力。富士康18年的经历,让我深度理解生产制造,但这只是数字化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我在富士康积累的产业知识,以及对行业的认知,最终促成我构建出了自己的一套对于工业数字化从理念认知到转型抓手再到灯塔工厂建设系统化路径的完整体系,这也是我们灿态最核心的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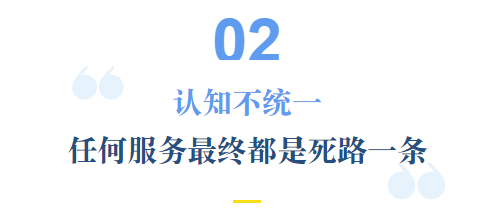
南方+:离开富士康创业后,你们遭遇到哪些挑战?服务中小企业与服务富士康相比,有什么不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最大的痛点又在哪儿?
宋勇华: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坚定地认为,我在富士康18年积累的产业知识,就是我的本钱。所以,我在与客户接触的时候,讲的也是富士康成功的、经过验证的经验。
后来我发现,国内90%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比起行业龙头晚了5-10年而大量的服务商就和我一开始那样,就是做数字化的搬运工、经纪人,把之前在龙头企业成功的经验套用给中小企业。

但是,客户经常反问我,数字化我们不反对,你讲的也很好,但是我们不是富士康,我们从哪里切入,要花多少钱?
简单的说,就是龙头企业的转型经验,并不完全匹配中小企业的转型需求。而他们之间的差距,就是认知、成本和基础。
首先是认知问题。作为服务商,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企业问我们,什么是数字化?数字化能给我的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想想看,从老板、经理、车间主任到一线员工,所有人对数字化的理解程度都不同,好比是从小学、初中、大学水平不等。统一认知,到底需要数字化实现什么样的价值,是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当企业内部对数字化的认知不一致时,无论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都是死路一条,因为总会有人反对你。
再者,在数字化转型中,比起软件,中小企业首先需要的是一条顺畅的生产线。很多企业的生产线规范程度,合理性,远没有做到最优化,甚至有时候,他们连IE部门都没有,仅凭一套软件对企业的生产管理起不到决定性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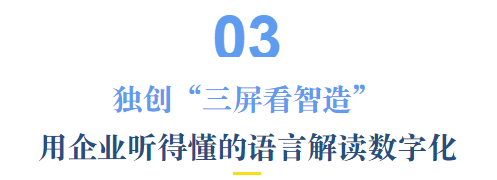
南方+:如此说来,数字化转型首先就是要建立一套能够满足不同认知水平的解释。作为服务商,你们是怎么做到统一认知的呢?
宋勇华:必须要把在大企业沉淀的知识,拆成中小企业能听得懂的语言,在理念上做革新,重新解释数字化。所以我自己创造出了一套数字化的理念:“三屏看智造”,让看板成为智能制造落地的眼睛和载体。
何谓“三屏看智造”?老板的手机,是第一屏;高管的电脑显示屏,是第二屏;生产车间大看板,是第三屏。简单来说,就是将智能制造过程呈现在三块屏幕上,实现企业经营高层、管理中层和车间基层的互联互通,通过三屏信息的互通与协调,打造智能制造的第一战场、战情室、指挥部。
具体到每一块屏幕,生产车间的看板屏幕上,体现工厂每一条生产线实时的生产情况,方便车间组长安排当天的生产工作;中层干部通过电脑客户端,可以看到不同厂区的生产进度,能够掌握一周、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生产计划;企业老板在手机客户端上,就能看到每个订单的进度、产能乃至利润,他一边和客户喝着茶,就能把新的订单定下来。
三屏的背后,必须将现场的生产流程全部数据化,5秒钟实时更新,从而抹平信息时间差,扫除数据的灰色地带。其次,通过三屏一体化的信息化监控系统,企业能够从整体到细节掌握生产经营全过程:发生了什么资讯,部门之间怎么去推动互通,就能掌握整个生产的逻辑,产能效率、产品品质、组织协同,就能得到全面提升。
说到底,为什么企业内部对数字化的认知会有那么大的落差?因为不同的职能部门,关心的内容都不一样。老板关心的是生产、品质、财务、设备的主要指标,生产经理需要掌握产量产能、产品质量、人机效能;车间组长就想搞清楚,今天要生产两千部IPhone,到了中午产能还没跟上,那究竟是备料不够、人手不够还是设备不足?他要知道下午重点关注哪一个生产环节。
而“三屏看智造”,就把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说的简单、通俗,从老板、总经理到车间主任、生产组长都能听得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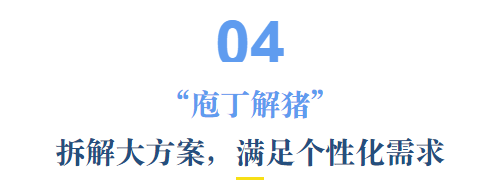
南方+:“三屏看智造”的确通俗易懂,且耳目一新,那你怎样将这个解读,具体转化为中小企业需要的服务呢?
宋勇华:就像前面讲的,富士康是做系统性整体方案的,好比像养猪专业户养了一头整猪。但中小企业关注的是并不是整体,而是是否能解决某个痛点,是否能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换句话说,中小企业要的不是一头整猪,他要的可能是猪蹄花,也可能是猪头肉、猪尾巴。因此,需要整体统筹,把18年来在富士康沉淀的产业知识模块化,分期分批地推向大批中小企业。就好比说,我把一头猪宰了,去卖猪头肉、猪蹄花、猪尾巴,来匹配各企业的不同需求。我把这个过程解释为庖丁解“猪”。

但是,不管是卖整猪还是解“猪”,本质的东西就是三个字:采、析、显。
采,解决数据来源,这里要解决数据的完整性、正确性和经济性。尤其是经济性,如果花100万的钱采集价值20万的数据,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有些企业应用AI短期反倒造成亏损,就是你花大钱采集的数据性价比太低,不符合市场经济;析,就是这么多数据给甲方不同职能部门,他们怎么样看到价值,怎么样帮到他们的工作;显,就是怎么样方便地显示出来。
围绕“采、析、显”,我们研发出了不同的模块化产品。比如在“显”这个环节,我们研发出了“鹰眼云看板”Saas产品。与普通可视化看板产品相比,不需要IT的专业知识,也能轻松地绘制图表。在富士康工作了18年,我很清楚不同部门的负责人需要的数据可视化图表是不一样的,如果每一个图表都要重新开发报表,那将会带来非常大的工作量和系统投入。所以我们在看板中预设了图表模型,根据信息展示需求,支持客户DIY配置,鼠标一拉一画,就能生成不同的图表数据,大大降低了使用门槛。
将一整套数字化的理念拆解,将产品模块化,用小产品精准切入中小企业的需求,就是庖丁解“猪”。而当生产效率有明显改善,中小企业也将会继续寻求更深入的数字化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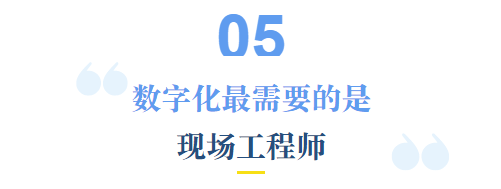
南方+:现在谈数字化转型,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政策、人才、技术、软件。您是怎么看?
宋勇华:确实,现在谈起数字化,很多人谈的首先是技术。但其实,技术只是为你所用,并不是你独有的,任何企业都可以引入最新技术,人人得而可用之。所以技术不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竞争力。
另一方面,各个地区也在引进博士、院士、专家、教授这样的高端人才。但是第一,高端人才在全国数量有限,属于存量市场,第二,因此,需要整体统筹,高端人才是流动的,其价值主要在于观念引领和行业推动,所以我认为,只有高端人才还是不够的。
再说软件,我们前面说过,中小企业数字化的基础比较薄弱,绝不是导入一套软件就能实现全面数字化的。
这两年,我们在服务中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因素,不只是技术,高端人才,软件产品,还需要贴身落地服务企业的现场工程师。一个企业里面数字化想要落地,最迫切的是要有一两个懂数字化的现场工程师,他们才是保证数字化落地持续推动的最后一公里。但他们是被我们忽略的一个人群,也是现在数字化转型最缺的人才。
其实,国家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人才结构性失调的问题。近日,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通知,决定联合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到2025年,累计培养不少于20万名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现场工程师。

南方+:那么,灿态这几年的创业,有没有为工程师人才的培养做一些努力?
宋勇华:坦白说,我现在无法解决这个工程师匮乏的问题。我只是结合灿态服务的客户做了一点改善,一方面解决灿态服务企业的工程师需求,比如说,你购买我的服务,我“送”你现场工程师。我会融合那些了解制造业的生产流程,熟悉生产数字化系统的优秀人才,能够很快地培养成现场工程师,输出给客户;或者,为客户提供现场工程师培训,将他们原有的员工培训成现场工程师,确保灿态前期技术人员离开公司后,这套产品能够继续正常运转。但这些都只是小范围地服务灿态的客户企业。

南方+:龙华区正在全力建设“深圳数字经济核心区”,你觉得,这方面,龙华可否有所作为?
宋勇华:其实,龙华区制造业土壤肥沃,以富士康、华为等龙头企业为圆心,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制造业产业生产体系。在行业龙头的推动下,供应商企业也具备了一定的数字化意识和基础。此外,这几年深圳产业升级,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留下的企业普遍有危机感,谋求转型升级。可以说,龙华区是兼具先天的基因和当下的需求,完全有培养现场工程师的基础。
所以,作为龙华区政协委员,我目前正在参与一个提案:“数字龙华”可以响应市场需求,建立自己的现场工程师培养体系。
例如,在引进数字化专家的同时,推动现场工程师的培养,招募相关企业骨干、社会人士、高校毕业生等人群,推出数字化基础培训短期班,以“周末工程师”等形式来培养现场工程师人才,结业后颁发受政府认可的数字化现场工程师的等级证书,为龙华区、深圳市的数字化转型推动现场工程师做储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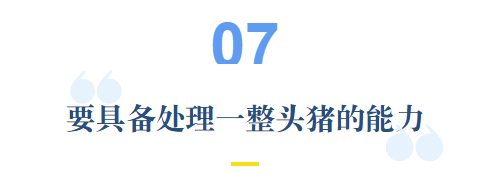
南方+:我们注意到,您在2022年4月出了一本书,专门讲述《打造灯塔工厂》,这不是一般的服务商做的事情,您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宋勇华: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从易到难、由点及面的,随着转型逐渐深入,会有一批中小企业脱颖而出,成为本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标杆。而在树立标杆的过程中,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我是“养猪专业户”出身,具备“处理一整头猪的能力”。
什么意思呢?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虽然是从具体的痛点切入,但最终仍然要走向系统治理。而我们在富士康的18年,沉淀的是数字化转型的系统的知识、经验,是对整个行业的认知。
“灯塔工厂”代表当今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中国有42座灯塔工厂,位列世界第一,而富士康则是全球电子科技制造服务领域唯一拥有4座灯塔工厂的企业。近日,工信部提出,中央财政计划分三批支持地方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打造4000-6000家“小灯塔”企业作为数字化转型样本,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转型典型模式。灿态也是第一批被评为国家工信部“小灯塔”的服务平台。从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到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树立标杆,我希望灿态能够具备打造灯塔工厂顶层规划的能力,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乃至灯塔工厂的打造贡献力量。
所以,我就写了这本书——《打造灯塔工厂》,系统介绍了运用先进技术并产生了规模化效益的灯塔工厂,总结他们的转型路径和技术模式等经验,推动中小企业“看样学样”,加速转型。
